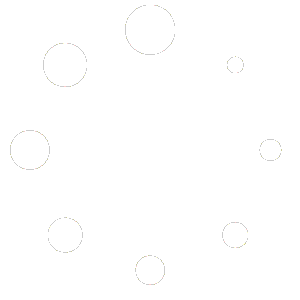作者:曼提柯尔百里
我曾度过了荏苒苍华的岁月,记不清有多少历史翻云覆雨,三国乱蜀中园,盛世大唐、明清民末,甚至是无数的乱史瑰丽的异世,不复华年。
在每段历史中又走过了大江南北,塞外孤烟群狼北望、犬戎羌笛雪落穹宇。江南墨染酝出一方梅雨纷纷。南非看惯了日落,法国酒庄里把玩着酒杯,透过红酒细数时代的光影。无论是埃菲尔铁塔亦或是远渡海洋之后的金门大桥,我总是裹着一袭风衣,在匆匆人影里,一直追随着某个身影,却也一直孤独困苦。
追溯记忆,似乎充斥了漫过边际的灰暗。
我是他的奴隶,以前是、现在是、以后也是。
兽亦握着枪柄,头盔已经被挑落不知去向,虽未曾负伤,脸上却沾满了飞溅而来的热血,这会儿已是呈现暗褐。
城池之中,百姓早已被驱散逃之夭夭,将士却不能弃城不顾,只因过了这境,不远便是京都。
身在厮杀吼声之中,无人注意到有只沾染血污毛发早已不是白色的犬兽小兵,不远战鼓擂擂,是敌军所向,那头跨于战马之上的白狼犹如凶兽压境,愈战愈勇。
将军身旁已经不剩多少还站着的士兵,兽亦踩着尸骸逐渐靠近将军。
正了正衣冠,将军的虎眸内敛,沉默的看了这只根本不曾有过印象的小兵,到嘴的话只化为点头。
长枪疾射而出,似有龙吟低亢,又好像整个天地放慢了许多,晃了兽亦的双眸。
不过一回合,将军身陨……原本要被围剿上来的敌军乱枪捅死,当头那个被一脚踹翻。
“杀了他又不能怎样,留作奴隶当工不是更好?”
兽亦的眼前仿佛还残留着那道枪影,拔出后血洒三尺。愣愣的低头看着双腕被牛皮筋紧缚,拴在马尾后,在经过敌军将领那只白狼时,忽然低吼。
“给个痛快,士可杀不可辱,你们的将军也只不过是用了阴谋伎俩才取胜的!”
战马喷了个响鼻,跨于马背上的白狼一身银甲峥嵘,缓缓侧过头,垂下的目光盯着那头躲闪不过他的眼神只得狠狠回应的犬兽,竟是细思端量了一会儿。
掌腕间挑了个枪花,在兽亦完全反应不及时,长枪抵在他的下巴上,迫使他慢慢抬起头颅。
“奴隶不需要多言,舌头不想要了割掉便是……我是你的主子,记住了。”
收枪勒马回身,在兽亦并未细觉那后半句的意思时,忽然手腕一紧,踉跄几步后无奈只得迈开步子拼命的追在身后,留下马蹄硝烟不绝。
兽亦被脑袋朝下直接扔进桶里洗净,硬毛刷子原本是刷马厩用的,如今使唤在自己身上,只觉生不如死羞辱难当。洗净之后喂了药,恍惚里听到巫山云雨之类又听到房事之流的污言秽语。
每个当工的奴隶之前都是这样,灌了春药任由挑拣,不是死在矿山煤窑、不是死在修建城池,便是被玩弄致死于不间断的轮奸性虐里。
只是,推开厢门的竟然是他?那头白狼如今卸下将军的战戎,换上了一袭黑金镶边的长袍,无数个念头中,杀意与惊恐交叠,兽亦已经被一只脚爪踩在胸膛上无法起身,只能半坐在墙根,双腕间的锁链铮铮作响。
白狼将军俯身,爪子捏起兽亦的下巴,贴在侧脸上嗅了嗅。
“很不错的味道,洗过澡后已经不见了那种血腥气……不似本将军多少年了,已经洗不掉一身的战火。”
“杀了我,给、给个痛……”
拳风似是携着罡火,重重击打在兽亦的侧脸不远的墙上,歪着头瞥见凹陷处丝丝龟裂,面前的白狼将绽开皮肉的关节放在兽亦的嘴角,涂抹了几下之后,直起身走到门边,忽然扬了扬爪子。
“记住我之前说的……我叫莫问,但以后你只能叫我主人。”
刚拉开门,外头的夜风倒灌,门口有把守的士兵,不远垒着炭火,背后忽然传来怨毒的嘶吼。
“嘘,乖一点苦头会少一点,外头可有旁人在,不想被打个半死或是拖去当做狗奴一般性虐致死,嗯,就乖一点。”
“嗯,乖一点。”似是自言自语,低声中负手走下台阶。明辉皎月,莫问看着东南方向,那里是他守护的国都,却分毫没有惦念的身影。
三天了,并未走出这间不透光的厢房,每次送饭也是晚上,菜品简单却是分量足够,让饿了一天水米未进的兽亦并未多少考虑气节的问题,舔完盘子后便搁在一旁闭目养神,他考虑的仅仅只有一个。
那头叫做莫问的白狼如果再来,他会试图袭杀一次,如果失败他会立马寻死自尽,而在这之前兽亦必须养足体力。
这很疯狂不是么?身为被强行征兵不足三月的训练,握着长枪第一次杀人时也这样,不,现在理应更加疯狂无助,绝无退路。
三天过去,兽亦半梦半醒里忽然觉得一冷,慌乱睁眼顿时心凉,入眼是莫问有些微醺的用爪子挑开他的兜裆布,把玩着半垂的肉棒。
兽亦暗恨,自己为何会睡得如此深沉,眼下朝夕不保,明明该有机会……
“想杀掉我?呼……何来的自信?”
喷着酒气,莫问话语虽然无味,却听在兽亦竖起的尖耳中,顿觉满满的讥讽。
鬼使神差的抬起双臂打算用锁链勒住白狼的脖颈,只是那白狼微抬头颅,一把攥住锁链抵在兽亦的喉咙前,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“明天会换个地方,这里总归不方便,这几日前线战情瞬息万变,等急了?”
松开爪子,莫问指尖沾染了一丝兽亦沁出的淫液,手掌似是要抚摸他的脑袋,却被兽亦躲开。
“你刚说了战情瞬息万变……这几日还在打仗么?我的国家……”
不在意的收回爪子,莫问走到门前,就像头一天一般,沉默了一会儿,微哑着嗓音。
“不出一月,你的国家便亡。”
叩门声中,屋内连连惊怒,忽然低下声来的抽泣,渐渐化为呜咽低嚎。
原本是眼上带着黑布,却被莫问拆下,锁链披身脖颈上粗有二指宽的圆环延伸出的锁链垂下,与双足之间拷在一起,背负双臂,兽亦就是这种姿态被莫问牵着绳索拖曳穿过几处走廊,兜兜转转,迈进一间宽敞的房间。
房间内的桌椅被搬空,莫问亲自将兽亦压到墙根脚下,双臂被分开吊在墙壁上的圆环里,兽亦就那般只穿着破烂的兜裆布,双腿被支在腿弯下的铁棍迫使分开,羞愤难堪的挣扎了几下无奈停下。
兜裆布前又一片湿润,实在不想回忆这几日每到夜晚,药性发作后,兽亦根本无法抑制的性起,直到当天撸动射出最后是稀薄时,才喘着粗气沉沉入睡。
他握住身前的他有些纤细的指爪,下巴埋于颈窝,雨中嗅着润躁。
搭弓远眺,毫无经验的他本该由着身后的家伙找寻目标,却忽然羞怯的说了声我学不来。
箭羽穿透了不远麦田里的农户身躯,那头狼兽怔怔望着灰白天幕,草帽卷了几圈挂在麦梢。
“死吧死吧,都死吧……看啊,你杀人了,记住了,这是你第一次的杀人……你肯定记不住……”
湿滑混着冰冷的雨水,舌苔舔舐侧脸的惧意,童年的兽亦、成年的兽亦,还有那爬过人来人往的街头,被他踩在脚下的兽亦。
忽然的醒悟,好像生命里只有记住之类的命令,赏与罚,赏赐是解脱后的欲望高潮,惩罚是一场惊梦。
一如此刻他终于停下来,转过身冲着自己招招手,兽亦脱下衣衫,乳头挂着精致的铃铛,在人来人往的诧异里,跪伏在地爬了过去,摇尾乞怜,脖子上的项圈泛着冷泽。
也如很远的过去,那天已经记不清的面目身影,踩着被麻绳绑在十字架上勒住腿弯,蹲在地上被踩着鸡巴,脚爪拉扯搓弄,痛呼里又重现多年后在那间房屋里,莫问的眼前。
原来自己从童年就是个骨子里深刻奴性的玩物……鞭梢抵在兽亦的下巴,迫使他抬起头,迎上莫问的目光。
他的眸子是鎏金色,十分漂亮。他的眼底有一丝疯魔,冰冷无情的敛下视线。
鞭梢粗糙,生有一些倒刺,游走胸膛间,卷住兽亦的乳尖缓缓转动,压住皮毛紧贴肌肉,沁出细密的血珠。
单指从沟壑里滑下,数着腹部的棱角,指肚涂抹在兽亦已经硬挺微微摇晃的肉棒龟头处,沾染一丝淫液,像是抚琴一般,莫问的指背捋过青筋高涨的茎身,微微用力没入兽亦的穴口。
血顺着指肚淌下,在肉掌中酝开。兽亦浑身绷紧,痛的低吼继而转为呜咽。
“总要尝试的第一次,你看啊,过了之后你的屁眼儿便紧紧吸裹着我的整根指爪,肠壁的褶皱缓缓蠕动,想排斥却夹得更紧。”
莫问用鞭子缠住兽亦的脖颈,逐渐勒紧,压在耳畔轻声细语。
“你这只奴隶的命是我的,我希望松开之后就听到该听到的称谓。”
“做、做梦……呃啊!痛、好痛!”
兽亦使劲抬高腰际试图脱离面前这头凶狼的指爪,只是随着几声锁链交响,腰部的铁环束紧,勉强低着头盯着下身沁出的血染了莫问的掌心。
“畜生、脏货别碰我,拿开快拿开!”
揽住兽亦的后颈,莫问歪着头凑近,在即将落在兽亦唇角时忽然挪开。
“到底谁才是脏呢?已经是本将的奴隶,如此的不乖巧,接下来有苦头吃了。”
脚爪夹住兽亦的肉棒,搓弄几下后踩向地面,本是硬挺高耸的下身被迫压下碰触冰凉的地面,兽亦紧皱双眸,疼的不断握紧双爪。
看啊,你看身下这只奴隶多么的好看……洗净之后的皮毛洁白柔顺,竖着的双耳捏起来真舒服,还有张开双腿,垂下的鸡巴摇晃着甩出糜液……这只狗狗忽然让莫问生出几分兴趣,大掌捋着后背,一遍又一遍。
缓慢的让兽亦毛骨悚然,却又拼命抗拒,无奈跪着前倾的姿势,双腕并拢在一起被一条锁链捆住,脚腕亦是被地上打进的铁环铐牢,挣脱不得承受着后庭被一根涂抹香油的玉石圆柱抽插。
“喜欢我给你的礼物么?”
拨弄双乳穿进的圆环,悬坠着两枚精致的小铃铛,莫问坐在一把下人送进的木椅上,另一只爪子撑住脑袋靠在扶手边,眯着眼对着微微低着头战栗不止的兽亦说道。
尚在方才无法避开视线,惊惧的看着被火烛烫过的针头刺穿双乳,血线飚在胸膛和脸上的记忆中清醒,兽亦对于莫问的话听不真切,再度低下头颅,带着哭腔。
“求你、求你放过我好么……我只是个小兵,根本不能掀起什么风浪,将军大人便是把我发配到矿山煤窑做苦力也好,求你……”
“你叫我什么?”
从木椅上弯腰前倾,捏住兽亦的下巴迫使抬起,莫问盯着他脸上的泪痕,眸子里带着几分冷意。
“叫我什么?再说一次。”
“主、主人……求……”
“够了,非常好,以后也要主动一些。”
甩开兽亦的下巴,莫问直起身抻了抻懒腰,似是有些困顿,过了半晌忽然压低嗓音。
“我准许你保留你的名字……尽量的讨好主人吧,还能活的久一些。”
日子一天天的过去,记忆成了碎片,每个断层里似乎只有欢愉和痛苦,然后痛苦成为欢愉,贪婪的沦陷进去。
兽亦曾在角落里画着刻痕,数着日子,数着今天活着明日生死,后来就忘了那个地方,因为被这只口中称作主人的白狼看到,命令他不断的撸射手淫,用精液掩盖那几道刻痕。
前线还在打仗,兽亦的国家所剩的军队节节败退,已经不想去猜有多少儿时憧憬的威赫武将被莫问斩于马下,也许黎明到来前,国破家亡,从此无根无落。
他变得很忙,去的时候兽亦是昏迷,来的时候携着风月一身战火燎燎,他总是处于微醺。有时会折腾到兽亦哭着求饶,却不曾打骂,有时就抱着兽亦安静的待到外头渐白。
村子还在么?听闻天启国奉行寸草不留的杀伐之道呢……妈,如果一开始我们就逃得远远的,小亦也不会被掳进军队,现在又成了肮脏的性奴,整日供这只白狼淫乐。
整日?头颅无力的垂下,指尖从挂着铃铛的乳头上滑落,兽亦背靠着墙壁,饿的皮包骨头。
打仗啊,杀人啊,到处血流成河……他很忙,少则三四天来一次,多则像这样已是半月未曾来过,外头的看守松懈怠慢,而我却也出不得逃不掉,已经好久都没有吃过东西了,虽然每天都会送来两碗水……
快撑不下去了呢,为什么不去死呢……一如他捏着我的下巴,翡翠的眸子里好像看透了一切。
“你的眼里还是有着恨,很好很妙。”
这般想着,兽亦一头栽倒在地,呼吸微弱。门外传进的怒喝也听不到了,莫问一手提着染血青锋一手将兽亦揽在肩上,出了门踢开倒在地上的尸骸,冷哼一声。
兽亦张了张嘴,发出微弱的嘤咛,睁开眼一片黑暗晕眩,待到恢复清明,这才看到一片血色帷幔。
自己是躺在床上的,很舒适……费力的想要抬起爪子,听到一串锁链交响,扯了扯嘴角认命似得不再动弹。
那头白狼就在床沿,端过一碗热粥,虽是依旧冷着脸眉宇间总是暗藏杀伐,却是放到嘴边吹了吹,用勺子舀起放到兽亦嘴前。
“吃。”
兽亦张嘴咽下,微烫入喉,半碗下肚似乎有了一些气力,这才倔强可笑的侧过头避开莫问的视线。
只是下一刻,被子被掀开,一只肉掌摩挲着兽亦的鬼头,略带几分粗暴,很快就润湿了掌心。
“就让我这样死了多好。”
缓缓撸动这头白犬的肉棒,莫问摇了摇头,出口也是带了几分战火燎烟气息。
“我不准你死,你就不能死,阎罗爷也算不了什么……我让你死,现在就可以。”
“你他妈就是个疯子,疯子!”
兽亦忽然梗着下巴,声嘶力竭的吼叫,又弱下去自言自语般语无伦次。
“为什么要打仗,为什么要夺走我的村子,为什么我要和妈妈分开,为什么你这种十恶不赦的疯子会存在,要不断的折磨我……”
想要掩面却是不得,声嘶力竭的哭嚎,莫问目光盯着他一会儿,逐渐飘忽。
“你和我弟弟一样,总喜欢哭鼻子……以前很讨厌,虽然当我再看到他时,是从敌营里强夺回来的……眼被挖掉牙齿一颗不留的敲断,双腿的关节也是寸寸裂开……”
“你知道么?他就是和你一样的想法,厌恶排斥战争,幻想着天下大同,被你们国家的贱民蛊惑厮混一起才被抓住的。”
猛地爪子如钩攥住兽亦的脖颈,鼓胀的肌肉愈加饱满,甚至是狰狞凶厉。莫问凑得很近,阴冷的盯着兽亦恐惧的双眸。
“现在想死么?现在想死么!”
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一幕,莫问慵懒的躺在椅背上,搭着双腿,头颅向后仰着,露出冷若刀锋的棱角。
兽亦跪伏在地上,伸出舌头笨拙的舔舐莫问的脚爪,虽然笨拙却是仔仔细细的舔遍每一寸。
他真的很怕死,以往的决断都成了玩笑。抬起头,兽亦强挤出讨好的神色,眼底夹杂着惊惧,小声开口。
“主、主人……请调教狗狗……”
房间沉默了一会儿,莫问微微闭目,半晌才哑着嗓子开口。
“今天先就这样吧,过来给主人舔出来,然后把送进的吃食都吃干净就休息。”
握着入眼散发雄厚情欲气息的粗长,兽亦吞咽下口水,战栗的将之含在嘴里,十分不熟练的强迫自己适应深喉。
偶尔不小心牙齿碰到了,惊恐无措的望着莫问,只是看他并未有多少反应,似乎困顿一般,只是轻轻开口让他多用舌头卷住吮吸。
莫问向后仰着头颅,睁开眼盯着墙上悬挂的长剑,剑鞘朴实无华,红缨赘着玉环,莫问再度闭上双眸。
时间过去了约莫一炷香,随着兽亦逐渐适应,并且卖力的变换花样,时而吞吐时而含住囊袋一边吮吸,莫问终是生了快要欲望喷薄的感觉。
他就像是一柄青锋,血染在疆场,杀伐果决。哪怕是射出时,亦是凶悍冷硬的模样,抬起头盯着兽亦,微微挺胯脚爪勾起,低沉狼嗥间喷射而出,大量的白浊灌满兽亦的口腔,一部分冲进喉咙,一部分顺着嘴角淌出,而兽亦一时不适,似是呛到,精液流进气管从鼻子里竟是也喷出一些。
带着泪痕的脸被莫问从嘴里抽出的肉棒甩出最后几道浓浆覆盖,兽亦双爪撑在身后的地面,坐在地上充满了淫欲情色。
门开的声音,兽亦瘫坐在地上,像是被抽干了所有气力,淫糜的不成样子。半晌掩面,甚至无力再去揩掉脸上的污渍,死死咬住掌心忍住呜咽的抽泣。
忽然身子僵硬,整个身躯被一双铁臂横抱怀中,似乎触动了哪根心弦,愈加不住的颤栗。
莫问低着头看了披着一件毛毯的兽亦一眼:“我的狗狗总要干净的,去洗个澡。”
有别那日的粗暴嫌恶,兽亦没有被直接脑袋朝下的扔进木桶里,相反……莫问将他抱进时脚尖刚一沾水,忽然想到什么似得要抱开,一掌揽住兽亦一掌探了探水温,用水瓢舀起侧过头看向兽亦的私密处。
“上次出了不少血,沾水总归不是个好事情。”
兽亦闭着眼,睫毛因为恐惧而抖动,脸上的污渍被水流冲刷干净,感觉背后的莫问似是拿着什么东西,打了个激灵回想到那天被刷马厩的硬毛刷折腾的死去活来的场景,忽然泣不成声。
“主人,我可以自己洗么?我真的好怕……”
身后的莫问忽然停下动作,沉默着,让兽亦惊惧的无以复加。
“狗奴知道错了……狗奴……狗奴听话便是。”
莫问没回应,爪子里的海绵涂着皂角,仔细的给兽亦擦着身子,然后放在他的掌中,在沾满泡沫的颈窝里深嗅一口,鼻尖沾了些许白沫。
“自己弄吧,不急……”
他的语气冷淡,虽是极力掩盖,却总有那么一股疲惫。兽亦握着海绵愣了一下,默不作声的扶着水桶坐了进去。
“嗯?伤口不要紧?”
“没、没事的……狗奴那次出血已经过去足有月余,已经不疼了。”
唯唯诺诺的语气,莫问坐在木椅上,微微抬了抬眼皮,怔了一会儿,似是在笑又好似无动于衷。
“打仗打的久了,日子也过糊涂了……”
兽亦泡在水里,冷暖适中,让他想起儿时一些光景,许是怕泡久了惹恼莫问,转过头看去,竟是诧异的愣在那儿,莫问不知何时将木椅搬到木桶旁边,双臂搭在木桶边沿,睡了过去。
他睡觉的样子卸去了一些肃杀凶戾,露出些许的眉宇刚毅冷硬,垂下的毛发被兽亦泡澡时溅起的水花染湿,不自觉的让兽亦恍惚了片刻。
腕足之间的锁链在进来时便被卸下,这时候莫名的将爪子探向莫问的后颈,指尖锋利。
下一刻,脑海里幻想无数次的血溅当场没有发生,兽亦小心翼翼的撩开宽大的衣袍,露出几道狰狞创伤。
旧痕摞起新伤,皮肉外翻着,看呆的兽亦忽然眼前一花,手腕被一只有力的爪子攥紧继而放松。
莫问抬起头,盯着站在水桶里赤裸身躯的兽亦,一直盯到他语无伦次的说着求饶的话,莫问忽然起身,问了一句便走到门口。
“你识字么?”
“多、多少能看懂一些……”
“等我下次来时,除却做那些事外,我会亲自教你的……另外我会锻炼你那孱弱的身体,我这儿不需要太过脆弱的废物。”
直到莫问拉开门迈了出去转身关门时,兽亦突然低下嗓音问道。
“为什么?为什么要这样待我?”
门渐渐关上,光影让莫问的脸朦胧,那双翡翠的眸子波澜浩瀚,他嘴唇蠕动了几下,声音很浅却字字掷地有声。
“这是你最后一次的直面问我……你是我的奴,不是那些军妓……这些天你要好好吃饭,那些奴才我已经杀了,你若是被生人欺负,不必害怕,给我记住他们的脸,告诉我。”
告诉谁,告诉谁啊?
我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叫做绝望的崩溃,好和坏全都没分别。
我在做什么,骑在无人空巷他的腰上,举起的枪头刺下、刺下,扎破眼球的水,咬碎他的脖子,血溅一脸。
身下的狼是谁,疯癫里应该是我的主人,白狼莫问……然后我躺在地上,腰窝硌的发疼,背后身影翻过来双爪的指尖摁在我的眼下。
“醒醒……你有名字,我从来没剥夺过,你叫兽亦,记得么?”
记得、记得、……记得,我叫兽亦,你是我的主人……那死的凄惨的狼是谁?
是我的同村发小,投靠朝廷做了死士,杀不掉你,他就得死。
兽亦坐起来,抱住莫问呜咽,喉咙里的声音彻底成了魔,化为蛮兽。
这段记忆发生在何时?当场?几天后,还是几月城破亡国时……
在那之前,我因为随军跟他,一次动乱里逃了出来,然后被不知哪方的贼或军追赶坠下矮崖顺水漂到邻国。
兽亦醒来的时候,是在街头浑身赤裸的被绑在木架上,两股粗绳纠缠拧成麻花勒在脖子上,喘不动气,听着奴隶贩子……或许之前只是个无良却胆小的商贩,在这乱世当头,发了人头买卖的财。
他说这具犬的身体不知道被谁调教的真是敏感,五个铜板就让插嘴玩弄鸡巴虐一刻,散碎细银便能当街肏干一番。
然后整天在射和不能射的被迫里,想着谁能救他脱离苦海,想了很多,有自己国家的军队,有那头白发凶狼……
然后浑身被无数的手掌抚摸揉捏,磨破了乳头,磨破了茎身,红肿的吐着白浊,吃过了太多的鸡巴。
成年的、顽劣乡绅的、鳏夫老耆、还有领着孩童的父亲,摸出几枚沾染油污的铜板,摔在案板上,仿佛和那些出大价钱的一个响。
再醒来时,又像回到了初见的模样,他半蹲在地上,兽亦躺在莫问的臂弯中,目光游离。
莫问摸索着兽亦的身体,每一寸的皮毛下的血肉,闭目喘了口气。
“本将若是在他身上摸到不该有的痕迹,消不掉的话你们统统给我死……”
压抑的怒火让他话也带着矛盾,撕扯下衣衫缠住兽亦背在身后,莫问腰间赘着青锋,银枪流转,杀得血流成河。
找寻了三五日,刑讯宰掉不少的奴隶贩子,循着点滴线索只身潜入邻国。
生死啊,那是什么狗屁东西,莫问心里只记得,他的玩物任谁不得染指。
兽亦从莫问背上滑下,愣了一会儿,忽然埋头痛哭,终于沦为了肮脏的性奴,那头凶狼终究会嫌恶的杀了自己。
日光在兽亦身后的乱石间散开,兽亦瑟缩的靠在上面,莫问背对着他盘膝而坐,银枪横在腿上。
直到月升到枝头,莫问忽然轻声开口:“没有下次了……”
兽亦抱着双肩,脑袋埋在膝盖里,只露出一双还带着几分犹如惊弓之鸟的惧怕,竟是鬼使神差的低低嗯了一声。
往事随风,尘缘如梦。
战火蔓延一发不可收拾,往后的日子,兽亦不在那留下太多撕心裂肺的黑屋,搬去了莫问的帐下,时有军中将士看到莫问身边随着个清冷温雅的犬兽,一袭青衫白衣,端着袖口在磨墨。
却无人看到兽亦衣衫中,垂下根锁链,和颈上项圈相连,套在阳物根末。
归之为麻木也好,无心无力的去反抗,无谓后的欣然接受,渐渐看清自己的模样和本相。
帐中无人,外头唯有几处篝火,莫问轻掐住兽亦的下巴,冷硬的嘴角落在他的唇上,然后攥住兽亦的双腕抬起,锁在帐中垂下的锁链吊环。
拨弄面前即便到如今脸上也暗含羞怯模样的白犬乳尖,莫问指尖从胸腹滑下,穿过下身毛发一根一根的指节攥住兽亦半垂的肉棒,搓弄几下,俯身含住,带着极具侵略的狂躁和柔意并存。
似是不满意,兽亦头一次喘息着低头欲言又止,最终哑着嗓子开口。
“主人,狗狗想被调教虐待,想要更狠的惩罚……但是狗狗很怕……”
吐出尚在跳动的犬兽硬根,莫问抿着双眸,千百情绪从未透在外人身前,又伸出舌尖自下而上舔过兽亦的鬼头,汲取流出的淫液,惹得兽亦忍不住的绷紧身体。
“我告诉你个秘密……但在这之前,需要告诉你另一件事。”
贴在竖立的犬耳旁,莫问微微张嘴,话语随着吐气,艰涩微弱。
“放松,我说过你会成为我一辈子的狗狗……你知道一辈子有多长么?对我而言从未有过尽头,前朝或是更早,我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君王,形形色色的都看惯了。”
“你亡国了,尚有我在。三十年河东河西,如今这朝野也该到了气数尽枯的时候了。”
兽亦沉默了一会儿,摇了摇头。
“主人,狗狗不懂。”
“你会懂得,看着罢,陪在我身边,不用再在意除却我之外的任何,任何……”
莫问收回前倾的身子,站在几步开外略微歪着头望着兽亦,笑了笑,甚少的模样。
抄起桌上藤条编制的板子,莫问绕到兽亦的身后,用指尖掰住前段,松手后反弹击打在兽亦的臀肉上。
不轻不重,略有痛感,兽亦闷哼一声,下身更加的肿胀,不断流出淫水,顺着茎身汇聚在囊袋下,垂下银丝。
时而轻缓时而沉闷,皮毛之下的肉泛红,兽亦眼角夹泪,却是莫名的舔着犬牙无声笑了。后穴挤入的指爪如今能勉强没入三根,兽亦迎合着前后晃着身体,呻吟渐涨。
他终于低估了莫问曾说过的话,也终于明白其中的滋味……酣畅淋漓的享受主奴之间的快活,抛却所谓廉耻,毕竟莫问从那会儿开始,再没让兽亦为别的难过。
除了之后那场撕心裂肺的苦楚……
远远看着饥寒交迫的亡国难民,兽亦的眸子蒙上灰暗,莫问骑在马背上,回头扫了他一眼,似有无声叹息。
无根飘摇,风尘守在空枕,国和家都被一场烈火烧了三夜,雨下了三天。
目光探究着,又怕莫问的责罚,兽亦爪子缩在长袖里攥住衣角,然后蓦然寻觅到夹在流亡的纤弱身影,终究忍不住的蹲下来用力掩住面目。
不哭、不哭……
再也回不去,从此是个尚有亲故的孤儿。
莫问伸出臂膀,兽亦抬起头眼睛睁大,涌现无数的血丝,爪子搭在莫问的掌中,马上白狼略一施力将兽亦抱在身前,下巴在他的肩头来回厮磨,继而勒马回身。
终于明白了么?在漫长的年岁里,再也没有所谓的血脉情义能牵绊得了你。
扬鞭策马,一路西去东回,南来北往……自此兽亦看着莫问,他的主人那张冷硬的脸愈加的迷离烟茫,好像没有任何能再入他眼。
走过了很多疆域,有他驰骋塞北的威风八面,也有披星戴月大漠孤烟的绝尘艰涩。那时候,莫问只因兽亦在看到奴隶贩子组成的散队里虐待奴隶的场景,目光中的灰暗稍纵隐去,便是毫无缘由的屠戮干净,纵使棱角分明的锁骨下被箭羽洞穿,携着他再奔数里才倒下。
洞穴内,莫问起了高烧,这是从未有过的。兽亦戴着项圈,乳尖赘着精致的小银铃,在荒漠里寻到奴隶贩子们的水源,竟是不多。
喂了他水喝下,看他昏沉在兽亦搀扶下尿在坛子里,然后悄无声息的抱着坛子坐在洞穴外,靠着石壁皱眉嗅了一口刺鼻腥臊的尿液,兽亦继而摊开眉目,想着莫问以往和他的故事。
泯一口,日月乾坤在黄沙那头,拉扯自己的乳头。然后再泯一口,拴马绕着旋飞絮扑面,指节勒住茎身,放下坛子的另一只爪子探向穴口。
再也没有他物能让他倒下!兽亦终于明白莫问曾对他说的秘密,这是偌大宫城一角的偏殿。
莫问卸下战甲,裸着健壮上身紧紧箍住躺在地上的兽亦,汗水沁出迷了双眸。莫问的臂膀和后背,皮毛下现出道道血痕,兽亦咬着牙头一次真正的享受迎合。
外头喊杀声携着烈火升腾,他的预言终是再现,看给这九州天下的金戈铁马万世永存全都是个笑话,朝野权倾的荒淫无度,恶果天报。
砖瓦跌落,摔碎了,摔不破他已经无谓的冷血。莫问和兽亦全都到达欲望的顶峰后,莫问忽然抱起兽亦,听着喘息中怀中白犬的问询。
“主人做了这么多,真的要看着曾经峥嵘歃血立下汗马功劳的国家亡了么?”
莫问面上无悲无喜,一直抱着兽亦快要走出殿门时,这才开口。
“你忘了,这不是我的国家,未曾生养,我也没有留恋……和我一起在乱世里归隐吧,许你自由、许你欢畅……就是不能离开主人。”
旋梯如今成了悬魂梯,台阶下那曾经昭告天下为万古君王的他,坐在那里指爪交叉。
到了这会儿无力回天,也再无心思。他坐在那里,褪下皇袍。然后捋着胯间坠着锁链的玩物后颈的毛发,火涌上来。
“去吧……”
从玩物嘴里抽出阳根,帝王的他再过一会儿这皇城不再归他,牵着玩物颈上锁链,在转折处从掌中滑落。
“去吧……”
去哪儿呢?那头狼兽玩宠蹲在原地讨好或是嘶吼,在逐渐攀登的身影远去时,猛地向前扑去,换来他迎头踹下,从不离身的佩剑掷于身前。
所谓的千古帝王啊,他站在高筑之上,望着皇城烽火,望着城外黎明,随后化作焚火。
那头狼兽抱着佩剑,瑟缩的行在皇城内,似乎没有注意到背着兽亦行如疾风的莫问。
远有吆喝声传来,那狼兽一怔,莫问早已躲入墙后,望着一行将士提枪而来,狼兽咬牙抱着佩剑一头栽进熊火燃烧的房内。
兽亦看在眼里,再看看莫问的后颈,悠悠千古,华年不复。
从那刻开始,便是天下为敌,指着他骂沦丧不堪,他也要守在莫问、守在主人的身边。
这本该是错误的,畸形的……兽亦知道,却任由它扭曲蚀透自己。
这世上,再也没人能宠他一下,多看他一眼,这世上除了主人,再无念想。
边陲连绵险山,纵千万里长川。分出一条江汇,再入这里是一条溪流。
溪流前有座茅草屋,门后挂着整张皮毛,屋后有处篱笆院,种着瓜果石上坐着兽亦。
莫问放下肩头抗着的猎物,敲了敲墙,一头白犬风驰电火般闯进,然后蹲在地上蹭着他脚爪。
“留心脚下。”
略有些宠溺的抚摸兽亦脑袋,莫问扫过门口,停在河畔树前似乎出神。
已经几年了?不……或许已经过去了几个朝代,就连吃喝也索然无味起来。
莫问微微摇了摇头,俯身托起兽亦的臀肉,收起利爪指节伸进,抠弄几番掉出几枚圆珠,期间趴在莫问腿上的兽亦闷哼几声。
“主人……狗狗想要……”
撒娇般的赖在怀里翻来覆去,莫问嚼着一枚酸枣,在兽亦从他怀里钻出来,可怜兮兮的跪在面前摇尾乞求的样子时,莫问忽然扑倒兽亦。
罚他什么呢?又是该奖赏何物?
反剪双臂捆的结结实实,兽亦的双膝下用绳索吊起,腰后悬空。乳头佩戴的圆环连着细链,与茎身上的圆环栓牢,相互拉扯,鬼头下绑缚的铃铛作响。
很久之前原以为他珍爱的青锋宝剑,现在也被莫问似乎全然不在意的拿来,剑柄没入兽亦的后穴。
“狗狗应该怎么叫?”
“唔哇……”
不对,莫问蹲下饶有兴趣的用羽毛搔挠在兽亦的囊袋间,听着兽亦汪汪叫之后,拿出剑柄挺身将自己的肉棒送进去。
就这样该多好……在所有的事物索然无味前,安然享受。
那样的日子总会到来,雾都伦敦,长桥上一头带着兜帽的白犬撞开一对夫妇,在几声咒骂里头也不回的离去。
追寻,不知为何。那个喜欢整日玩弄和宠怜他的身影,仿佛躲着他一般,却又好似根本没在他眼里留下痕迹,从巴蜀陇川追到伦敦,每当停下脚步歇息时,那头白狼便会在人群那头回身冲他笑笑。
那笑涩的像茶……
真的好像是遥远的过去,在风雨的田野间,拼命的跑过去,喘着粗气挣断项圈,那头白狼张开双臂等他而来。
可现在到了所谓的现代,悠久的生命里汲取了深厚的知识,隐入大众里又游走边缘。
兽亦失落的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街头徘徊,却是被经过骑着自行车的虎兽塞进掌中一团纸。
诧异的搓开纸团,看了一眼便扫去难过。兽亦毫不犹豫的脱下衣物,身上依旧佩戴了链锁一类的东西,赤裸着身躯爬过街头,穿过避让的人群兽海。
不敢抬眼的颤抖伸出舌头,舔了舔面前的脚爪。
莫问起身,在低着头颅伏在地上的兽亦身边离去。
诸如此类的游戏,他就像是国王,而兽亦只是取悦国王的玩宠,敛去多年便抛却的羞怯,像现在一样,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最繁华的地段,帅气的跳起极乐净土,回身侧头眼中暧昧的留给不起眼的一角。
脱掉上衣露出健壮的身躯,舞尚未跳完,兽亦在一群欢呼中呆呆的看着长凳上的礼帽。
忽然有些委屈……
靠着小巷的墙,兽亦缓缓蹲下,抱着胳膊忽然的泣不成声。
雨中走来执伞的身影,朦胧里一点猩红,那把伞倾向兽亦的上方。
“淋了雨若是病了可怎么做我的奴隶?”
“主、主人……求你不要离开我,狗狗会听话的。”
离开?那身影想笑,却发现自己已经没了任何情绪。莫问终究张了张嘴,轻声开口。
“随我回家……”
成都边郊的一栋房子,卧室的床上兽亦趴在上面,四肢向后捆缚一起,嘴里叼着口球,尾巴想摇摆几下却是不得,后颈延伸出的绳索绑在尾尖。
莫问打碎蛋壳,想了想又放下一个,围着围裙关上了水龙头,一滴水在盆里荡开涟漪。
端着盘子走进卧室,将餐点放在桌上,莫问坐在床边,挑起兽亦的下巴。
“毛手毛脚打碎碗碟,罚你龟甲缚一整天,现在吃点东西。”
卸下口球,望着跪在床尾扒着鸡蛋卷的兽亦,莫问看了一会儿,在不经意的泯唇间,蓦然发觉有了一丝甜意。
房间内一头白犬趴在地上,靠着白狼伸出的脚爪,似乎往日的悲欢离合烟消云散。
兽亦用力敲打下最后一个符号,起身接了杯水。
写下这个故事,回头翻看觉得糟心无比……若是有人看到定会说为了虐而虐,真是假的不得了。
那没什么,兽亦含住面前的狼根,深喉吞咽……我所经历的,就发生在眼前。
莫问……主人,他是我的神明,唯一而不能叛逃。